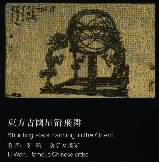版 主 自 述 |
| 个人简介 |
| 业余简历 |
| 彗星的发现和流星雨观测 |
| 学术活动 |
| 我的家庭 |
|
姓名:周兴明,1965年3月出生于新疆博乐军垦农场,籍贯:福建连城,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1985年在阿拉山口气象站从事地面气象测报工作,93年后在博州气象局从事过业务管理、天气预报声像系统、编播系统二次开发等工作,后又参与单位的9210工程(气象卫星综合应用业务系统工程)建设,目前为博州气象台计算机网络管理人员,从事计算机网络维护管理及气象业务应用软件、网络服务系统的应用开发等工作。 业余简历1979年在爱好天文的大哥影响下开始步入业余天文观测领域,初期主要从《天文爱好者》杂志、《天文知识》、《星座与希腊神话》、《小行星漫谈》等书刊杂志中学习天文知识,并结合星图认识星空,初中毕业时已认识北天的主要星座,读高中时还自制了简易的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1983年5月11日向紫金山天文台发出一份兄弟俩独立观测到“荒木-阿尔柯克彗星”的电报,从此将业余天文的主要方向转到了彗星的发现和观测上。 1985年从兰州气象学校毕业后开始了正式的寻彗观测。从1985年9月1日至今(2000年3月8日)已累计寻彗观测1484小时。流星雨观测50多小时。
|
寻 彗 历 程 1983年5月份对“荒木-阿尔柯克”彗星的独立观测是后来从事系统寻彗观测的一个开端,可以说这时已经给自己制定了今后业余从事寻彗这一天文爱好的方向。 从1985年9月1日至1989年5月14日用测风经纬仪进行了433次,累计464.5小时的寻彗,独立发现3颗新彗星。虽然均晚于国外天文台或天文爱好者,却得到紫金山天文台专家、教授的高度评价,其中,我的首次发现(1985年10月17日)被确认为新中国第一个业余发现。(参见《天文爱好者》1986至1987年相关文章) 1989年6月22日是我的150mm寻彗镜制作成功并首次投入使用的日子,从此告别了与国外高手在仪器性能方面相差两个量级以上的历史(80至100mm是一个量级),与国外爱好者站在了相近的起点上,真正参与到了“发现彗星”这一国际性的业余竞赛当中,89年到90年也是我十多年来业余寻彗的顶峰,1年半的时间里独立发现6颗新彗星:89年9月22日(差1个月)、11月28日(差11天)、90年1月16日(差两个月)、3月19日(差3天)、6月19日(差1个月)、7月16日(差5小时),特别是这7月16日(UT)的发现,差一点获得彗星的命名权(也是发现者所有权),按当时彗星的命名规则,一颗彗星最多可以三个人的姓氏命名,本人正好排在第三位,可惜当时阿拉山口通讯条件太差,本来报告就晚,电报又中途经手多人误了时间,等到紫金山天文台行星室的天文学家们收到报告时,已经收到了国际天文联合会(IAU)发出的彗星命名通报(电传)数日,天文学家们抱着一线希望,将本人的报告转发到IAU,IAU的专门机构CBAT(天文电报中心)的专家们经过讨论认为:命名通报已发,不宜更改,否则会引起混乱。紫台的天文学家们将复函的复件寄给了我,并转来了美籍华裔天文学家邵正元教授的一封亲笔信,对本人予以鼓励。在90年10月号《天文爱好者》杂志上,紫台的天文学家特别撰文予以通报表彰。 从90年以后至今,我又取得过8次独立发现,仍然晚于国外数天至1个月左右,现在我已注册进入了INTERNET,获取信息很快,相信这类无效的独立发现会很少了,这是好事,将能以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有效的观测发现上。
流 星 雨 的 观 测 我的流星雨观测最早始于1986年8月12日对英仙座流星雨的观测,之后又先后开展了对10月猎户流星雨、5月宝瓶流星雨、1月牧夫流星雨、10月天龙流星雨及著名的11月狮子座流星的观测。九十年代以来又尝试在寻彗观测的同时进行望远镜流星的观测记录,已积累数百小时的资料。 十多年来,流星雨观测作为我业余天文的“副业”累计观测资料约50多小时,尽管时间不多,但在全国还是排在前几位的,由于观测规范,内在质量高,被国内、国际上多位天文学家引用在学术论文中。 由于在猎户流星雨监测中的表现突出,1992年被中国天文学会普及委员会作为国内唯一在国际流星联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爱好者通报表扬。 1996年,因本人在流星观测方面的影响,被中国天文学会聘为九十年代强流星雨工作组成员。 1998年9月,中国天文学会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流星工作会议,会上对流星雨观测方面有国际影响的3位爱好者进行了表彰,本人是其中之一,奖品是紫金山天文台特制的两块流星雨观测纪念金卡(24K镀金)。 1998年10月8日,我偶然对天龙流星较强烈暴发的观测资料是全世界最接近主暴发时间的两份报告之一(另一份是日本爱好者提供的)对分析该流星雨自1947年以来的再次暴发情况起了重要作用,(参见国际流星组织网页:WWW.IMO.NET)得到国际流星雨研究专家rainer先生的重视,发来数封电子邮件予以鼓励。 1998年11月18日的凌晨,狮子座还是出现过一次预料之外的以火流星为主的暴发现象,当时,我没有计划观测流星,而是想进行寻彗的,因发现强烈的火流星暴发现象而中止了寻彗,临时进行了流星观测,结果获得了一份很宝贵的资料,因为我的位置在中国西部,观测的时间是国内距火流星雨暴发的极值时刻最接近的,国内有关专家对本次流星雨在中国的暴发强度作出的240多颗(ZHR)的结论正是基于本人的这份报告。该资料的价值也得到了国际流星雨专家rainer先生的肯定。 在1999年11月18日的凌晨,本人进行了3小时10分钟的观测,记录到狮子座流星205颗,其它流星22颗,从事后了解的情况看,本人是当天国内看到流星最多的爱好者,取得了一份国内最接近流星暴雨极大时间的资料。
|
|
1991年11月底至12月初曾应香港天文学会邀请赴香港参加“91天文学术交流营活动,在港逗留一周,接触了学会负责人和不少天文同好,并与香港观天会、澳门天文学会进行了交流,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下面是我们全家千禧年的留影,看看吧。 |